我刊2024年第3期發(fā)表的文章《論刑法中的結(jié)果型情狀要素》���,被中國(guó)人民大學(xué)復(fù)印報(bào)刊資料《刑事法學(xué)》2024年第8期全文轉(zhuǎn)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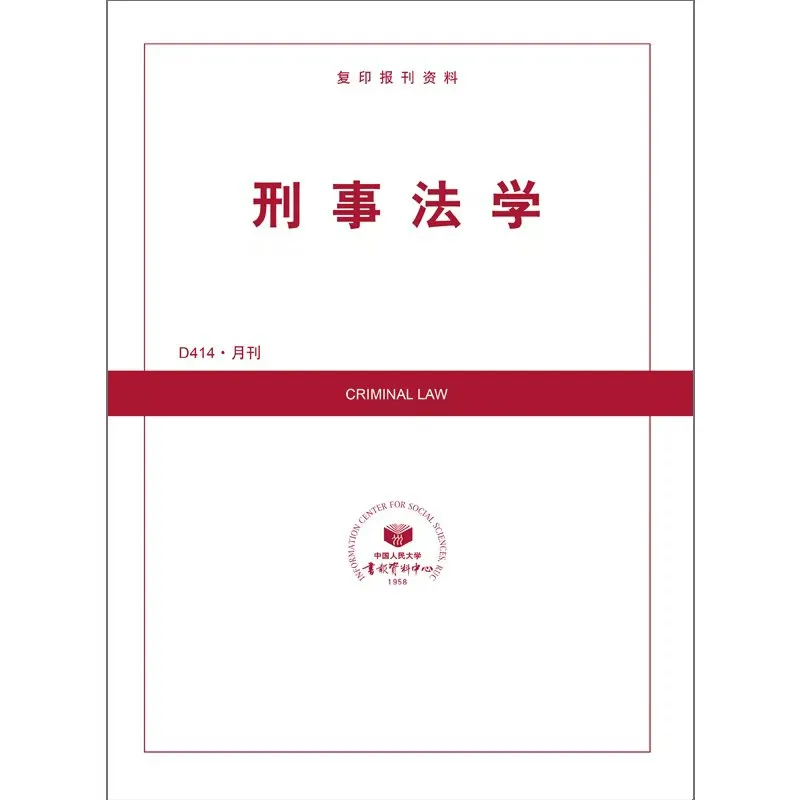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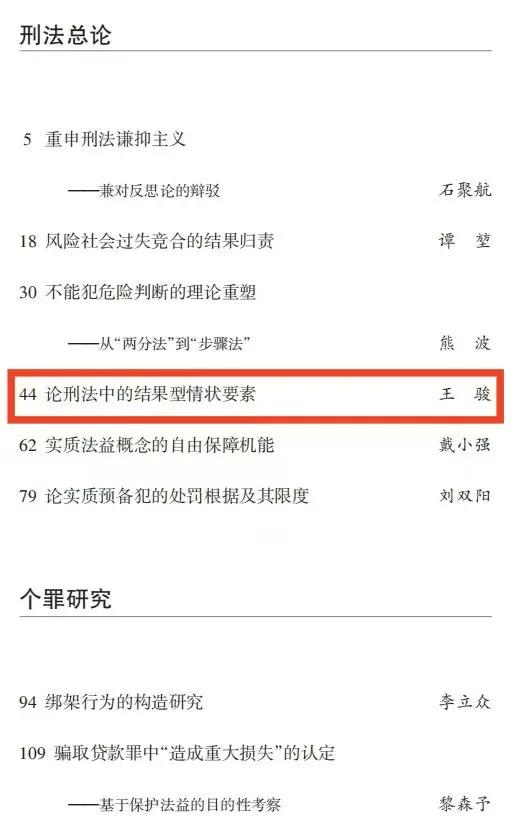

作者簡(jiǎn)介:王駿�����,男,湖北鄂州人�����,南京財(cái)經(jīng)大學(xué)法學(xué)院教授���,法學(xué)博士��,研究方向:刑法學(xué)�����。
摘要: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的“不典型性”在于描述的并非“結(jié)果本身”���。甄別“結(jié)果”與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,必須在法益探尋的基礎(chǔ)上進(jìn)行融貫性審查��。經(jīng)由因果關(guān)系和結(jié)果歸屬的檢驗(yàn)���,與行為之間不具有條件關(guān)系或不符合通常結(jié)果歸屬要求的結(jié)果要素��,都是結(jié)果型情狀�。結(jié)果型情狀的存在目的,不在于表達(dá)特定法益侵害結(jié)果���,不能據(jù)此直接導(dǎo)出所謂法益���。即便采取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立法模式,仍有必要堅(jiān)守“結(jié)果刑法”的理念����,“行為導(dǎo)致結(jié)果”的歸責(zé)條件不可放棄。在部分抽象危險(xiǎn)犯中�,危險(xiǎn)結(jié)果發(fā)生“本身”無(wú)法直接表述��,只能通過(guò)某種結(jié)果型情狀作為“中間項(xiàng)”來(lái)間接表征�。在部分抽象危險(xiǎn)犯中,結(jié)果型情狀只是單純限制處罰的條件��,但難以在犯罪論體系內(nèi)實(shí)現(xiàn)邏輯自恰�,在立法論上需要再審視。在部分侵犯?jìng)€(gè)人權(quán)利的犯罪中�,結(jié)果型情狀能發(fā)揮對(duì)既有實(shí)害結(jié)果的“違法性補(bǔ)強(qiáng)”作用。
關(guān)鍵詞:結(jié)果型情狀���;結(jié)果歸屬�;抽象危險(xiǎn)犯;中間結(jié)果�����;處罰條件
一�����、問(wèn)題的提出
在以法益侵犯為核心概念的《刑法》中�,分則各罪建構(gòu)了一套完整的行為規(guī)范體系,要求規(guī)范相對(duì)人避免采取侵犯法益的手段�,體系的形塑基礎(chǔ)在于立法者依據(jù)經(jīng)驗(yàn)法則確認(rèn)法益侵犯的發(fā)展路徑,據(jù)此在法條結(jié)構(gòu)中設(shè)定一系列的構(gòu)成要件����。不過(guò),法益本身是抽象性的關(guān)系概念�,現(xiàn)實(shí)上難以感知某種法益受到侵犯的狀態(tài)為何,所以有必要通過(guò)不法構(gòu)成要件中的結(jié)果要素予以表達(dá)����,從而將法益與人類既有認(rèn)知基礎(chǔ)上的經(jīng)驗(yàn)性狀態(tài)相連接。結(jié)果發(fā)生是我們判斷外部世界如何變化的關(guān)鍵�,涉及到客觀認(rèn)識(shí)性及經(jīng)驗(yàn)性的評(píng)價(jià)功能,結(jié)果要素在不法構(gòu)成要件理論�、法釋義學(xué)以及結(jié)果歸責(zé)理論的發(fā)展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“起點(diǎn)”角色�����。
刑法理論通說(shuō)認(rèn)為�����,結(jié)果是行為給《刑法》所保護(hù)的法益造成現(xiàn)實(shí)侵害事實(shí)與現(xiàn)實(shí)危險(xiǎn)狀態(tài)�����。以對(duì)法益的現(xiàn)實(shí)侵害作為處罰根據(jù)的犯罪屬于實(shí)害犯��,以對(duì)法益侵害的危險(xiǎn)作為處罰根據(jù)的犯罪屬于危險(xiǎn)犯��。實(shí)害犯中的“實(shí)害”是典型的結(jié)果要素�����。至于危險(xiǎn)犯,通說(shuō)認(rèn)為作為危害結(jié)果的危險(xiǎn)僅指具體危險(xiǎn)��,而不包括抽象危險(xiǎn)�。具體危險(xiǎn)是指危險(xiǎn)程度較高,使法益侵害的可能具體地達(dá)到現(xiàn)實(shí)化的程度�,這種危險(xiǎn)屬于構(gòu)成要件的內(nèi)容��。抽象危險(xiǎn)犯是指行為本身包含了侵害法益的可能性而被禁止的情形���,這種危險(xiǎn)是立法者的擬制,不是作為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的危險(xiǎn)�。據(jù)此,作為“構(gòu)成要件內(nèi)容”的結(jié)果要素是指作為“實(shí)害”和“具體危險(xiǎn)”的要素���,或者說(shuō)“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”就是指實(shí)害和具體危險(xiǎn)�����,所謂的“結(jié)果犯”也是指實(shí)害犯和具體危險(xiǎn)犯�����。例如�,《刑法》第115條第1款中的“致人重傷�����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財(cái)產(chǎn)遭受重大損失”是對(duì)“實(shí)害”的描述��,第114條中的“危害公共安全���,尚未造成嚴(yán)重后果”是對(duì)“具體危險(xiǎn)”的描述����。相應(yīng)的,第115條第1款規(guī)定的放火等犯罪屬于實(shí)害犯���,而第114條規(guī)定的放火等犯罪則是具體危險(xiǎn)犯�。
但是����,在我國(guó)刑法分則中,存在諸多“不典型”的結(jié)果要素規(guī)定�����。一方面�,這些要素從表面上看是對(duì)某種“結(jié)果”的表述,容易被誤解為典型的結(jié)果要素�����;另一方面��,基于各種原因���,其又不是典型的“結(jié)果犯的結(jié)果要素”��。最常被學(xué)者們論及的不典型結(jié)果要素��,就是濫用職權(quán)罪中的“致使公共財(cái)產(chǎn)�����、國(guó)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”�����。對(duì)于這一“結(jié)果”要素地位的爭(zhēng)議��,肇始于對(duì)該罪故意射程要求的討論���。只要將濫用職權(quán)罪認(rèn)定為故意犯,同時(shí)將“重大損失”解釋為“實(shí)害結(jié)果”�,則行為人主觀上的認(rèn)識(shí)、意志必須包含該結(jié)果以及其與濫用職權(quán)行為之間的因果關(guān)系����。根據(jù)相關(guān)司法解釋,“重大損失”包括“造成死亡1人以上�,或者重傷3人以上��,或者輕傷9人以上����,或者重傷2人�、輕傷3人以上,或者重傷1人�����、輕傷6人以上”的情形�,在行為人對(duì)此等結(jié)果具有故意的情況下,以濫用職權(quán)罪“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”的法定刑處罰�����,難免抵觸罪刑相適應(yīng)原則�。不僅如此,如果行為人對(duì)“嚴(yán)重后果”不具有明知且缺乏相應(yīng)的意志���,就不能認(rèn)定為故意�,這也會(huì)降低濫用職權(quán)罪的成罪范圍��,使其幾乎與故意殺人罪����、故意傷害罪等罪規(guī)制范圍相同,從而產(chǎn)生對(duì)該罪立法意義的質(zhì)疑��。造成這樣的現(xiàn)象���,主要原因在于“重大損失”是否一定必須解釋為所謂“實(shí)害犯的實(shí)害結(jié)果”�����。對(duì)此��,學(xué)界展開(kāi)了積極的探索����。一種觀點(diǎn)主張�,“重大損失”是限制處罰范圍的“客觀的超過(guò)要素”,不要求行為人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(jié)果發(fā)生���;另一種觀點(diǎn)認(rèn)為�,“重大損失”屬于罪量要素����,或類似于德日刑法理論中的客觀處罰條件����,無(wú)需納入故意的認(rèn)識(shí)范圍�。就該要素的地位,目前仍是眾說(shuō)紛紜���,未有定論��。
此外�,在以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“情節(jié)惡劣”為犯罪成立條件的犯罪中��,經(jīng)由司法解釋對(duì)“情節(jié)”的規(guī)定�,也會(huì)出現(xiàn)不典型的結(jié)果要素。例如�����,侮辱�、誹謗罪以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為要件,最高人民法院���、最高人民檢察院2013年發(fā)布的《關(guān)于辦理利用信息網(wǎng)絡(luò)實(shí)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(wèn)題的解釋》(以下簡(jiǎn)稱《網(wǎng)絡(luò)誹謗解釋》)第2條規(guī)定�,“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、自殘�、自殺等嚴(yán)重后果的”,屬于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�����。又如�����,尋釁滋事罪以“情節(jié)惡劣”或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為要件����。最高人民法院���、最高人民檢察院2013年發(fā)布的《關(guān)于辦理尋釁滋事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(wèn)題的解釋》第2條至第4條規(guī)定��,實(shí)施尋釁滋事行為�,“引起他人精神失常���、自殺等嚴(yán)重后果的”����,屬于“情節(jié)惡劣”或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。以自殺為例����,在上述情形中,司法解釋一方面將被害人自殺身亡的結(jié)果歸屬于行為人的行為��;另一方面又沒(méi)有讓行為人承擔(dān)故意殺人罪��、過(guò)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責(zé)任����。顯然,“被害人自殺身亡”并非典型的結(jié)果要素����。更為顯著的是,侮辱��、誹謗罪保護(hù)的是他人的名譽(yù)�����,難以認(rèn)為還包括他人生命��,使他人自殺身亡是對(duì)生命法益的侵害����,按照“結(jié)果是行為給《刑法》所保護(hù)的法益所造成的現(xiàn)實(shí)侵害事實(shí)”的定義����,致使他人自殺身亡也不可能是保護(hù)他人名譽(yù)的侮辱����、誹謗罪的實(shí)害結(jié)果。
不難看出�����,受制于通說(shuō)的結(jié)果犯二分理論����,不典型結(jié)果要素描述的不可能是實(shí)害犯的“實(shí)害結(jié)果”及具體危險(xiǎn)犯的“危險(xiǎn)結(jié)果”��。同時(shí)����,作為“行為危險(xiǎn)”的抽象危險(xiǎn)犯中也沒(méi)有容納結(jié)果要素的空間(行為犯同理),其屬性難免存疑��。本文稱這種不屬于傳統(tǒng)實(shí)害犯的“實(shí)害結(jié)果”和具體危險(xiǎn)犯的“危險(xiǎn)結(jié)果”的“結(jié)果要素”為“結(jié)果型情狀要素”����。一方面���,這種要素以“結(jié)果”形式呈現(xiàn),故稱“結(jié)果型”����;另一方面,該種要素又不是結(jié)果犯中的“結(jié)果本身”�,因而以“情狀”命名。本文擬在甄別“結(jié)果”與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的基礎(chǔ)上����,揭示其在犯罪論體系中的地位,同時(shí)就集體法益的構(gòu)造���、抽象危險(xiǎn)的判斷規(guī)則���、客觀處罰條件的存立意義等相關(guān)問(wèn)題發(fā)表淺見(jiàn),以求教于方家���。
二���、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的甄別
(一)法益探尋
既然結(jié)果是對(duì)法益的侵害或危險(xiǎn)��,那么��,要區(qū)辨“結(jié)果”與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�,離不開(kāi)對(duì)“法益”的理解�。或者說(shuō)��,不搞清楚什么是各罪所要保護(hù)的法益����,無(wú)從知曉某種結(jié)果是不是對(duì)該法益的“侵害或危險(xiǎn)”。要確定實(shí)定法中“結(jié)果”的屬性�����,就必須追問(wèn)法益為何�,這正是發(fā)揮所謂法益保護(hù)作為刑法解釋的指導(dǎo)原則的功能�����。從法益出發(fā)����,似乎是“繞不開(kāi)”的路徑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?擅媾R的問(wèn)題是����,這里的“法益”是“前實(shí)定法”的概念還是“實(shí)定法”的概念?
在立法論上��,“法治國(guó)刑法”構(gòu)成要件的創(chuàng)設(shè)���,必須受制于“行為刑法”“法益刑法”“因果關(guān)系刑法”的“三位一體”�,即《刑法》所能介入的必須是“行為導(dǎo)致法益受侵”這一“人際沖突”���,在此��,三個(gè)概念都屬于“前實(shí)定法”���。在立法層面,法益有體系批判功能�,即根據(jù)立法者認(rèn)為應(yīng)當(dāng)保護(hù)的利益種類和范圍��,法律被予以制定或認(rèn)可����,不具有值得保護(hù)性和需保護(hù)性的利益被置于規(guī)范之外����;在司法層面,前實(shí)定法益能指導(dǎo)構(gòu)成要件的解釋���,使得抽象的構(gòu)成要件在個(gè)案中被具體化�。前實(shí)定法的法益概念�,只是意味著法益的內(nèi)容即利益本身在實(shí)定法之前就已經(jīng)存在,法對(duì)這種利益確認(rèn)并加以保護(hù)��,就使之成為或上升為法益��。這就是所謂實(shí)定法的法益�����。不過(guò)�����,雖然法益是法前就存在的����,而非純實(shí)證的東西,但要探尋其內(nèi)容���,仍需要從法條出發(fā)�����。
方法論的法益概念則主張�����,解釋論層面的法益概念屬于一種后法益概念�����,法益是通過(guò)《刑法》建構(gòu)的����,是刑法規(guī)范已經(jīng)保護(hù)的范疇��,從《刑法》規(guī)定的構(gòu)成要件中可以發(fā)現(xiàn)法益概念。但是��,就后法益概念的解釋指導(dǎo)而言���,其效益是有限的����。因?yàn)樵诰唧w問(wèn)題上���,經(jīng)常是經(jīng)過(guò)解釋之后��,我們才知道個(gè)別刑法規(guī)定是要保護(hù)什么�,而不是我們先知道個(gè)別刑法規(guī)定是要保護(hù)什么����,然后據(jù)以解釋個(gè)別刑法規(guī)定的處罰范圍。到最后���,個(gè)別刑法規(guī)定保護(hù)什么����,和個(gè)別刑法的解釋是同一個(gè)問(wèn)題����,所以以保護(hù)法益作為解釋法律的依據(jù),具體而言��,是一個(gè)套套邏輯��?����!敖忉屨咴谔角髠€(gè)罪的保護(hù)法益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經(jīng)常聲稱是在追尋刑法規(guī)范的客觀保護(hù)目的�,但實(shí)際上,他們通過(guò)客觀目的解釋所挖出來(lái)的����,只不過(guò)是自己事先埋下去的東西,因而無(wú)非是一種更為隱秘的解釋者的主觀解釋���?��!币浴皩?shí)定法的法益”作為解釋“結(jié)果”屬性的依據(jù),是一個(gè)循環(huán)論證。
在超個(gè)人法益犯罪是侵害單一法益還是雙重法益問(wèn)題上���,陷入循環(huán)論證是學(xué)界常態(tài)��。以濫用職權(quán)罪為例�。有學(xué)者認(rèn)為���,“重大損失”與濫用職權(quán)行為要件相互獨(dú)立��,作為并列要件而存在�����,這意味著濫用職權(quán)造成的職務(wù)行為公正性受到破壞的后果本身��,不能歸入“重大損失”的范圍���,不然就不是并列關(guān)系而是同位或從屬關(guān)系;“重大損失”要件的存在意味著單一法益論存在不足���,將“重大損失”抽象化處理后�����,就提煉出另一重法益��,即公共利益或個(gè)人權(quán)利����。論據(jù)在于:一是“重大損失”是構(gòu)成要件����,所以是“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”;二是“重大損失”獨(dú)立于“使職務(wù)行為公正性受到破壞”這一濫用職權(quán)造成的后果�����?;谶@兩點(diǎn),“重大損失”指明了“職務(wù)行為公正性”外的另一重法益即“公共利益或個(gè)人權(quán)利”����。但是,這兩個(gè)論據(jù)都是“望文生義”而來(lái)����,經(jīng)不起推敲。其一��,從“重大損失”是構(gòu)成要件且描述的是某種結(jié)果,的確可以推出其是“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”�����,但某種“結(jié)果型”要素是構(gòu)成要件要素�����,并不意味著它就是結(jié)果“本身”�����,只有實(shí)害犯的實(shí)害結(jié)果與具體危險(xiǎn)犯的危險(xiǎn)結(jié)果才是通說(shuō)“結(jié)果犯的結(jié)果”���。因此����,如果“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”是指“屬于構(gòu)成要件組成要素的結(jié)果”����,所有對(duì)結(jié)果進(jìn)行描述的要素就都是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;但若“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”是指“結(jié)果犯的結(jié)果”���,對(duì)結(jié)果進(jìn)行描述的要素就不一定是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��?�!皹?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”概念的多義性��,決定了依托于它導(dǎo)出的“重大損失”的定位必然處在搖擺中��。其二����,并列規(guī)定的兩個(gè)要件完全可能是同位或從屬關(guān)系�����。如侵占罪中的“拒不退還”只是對(duì)“非法占為己有”的強(qiáng)調(diào)����,或者說(shuō)只是對(duì)認(rèn)定行為人是否“非法占為己有”的一種補(bǔ)充說(shuō)明,不是與“非法占為己有”相并列的獨(dú)立要素����。同樣,尋釁滋事罪中的“破壞社會(huì)秩序”也只是對(duì)列舉的行為類型必須具備“破壞社會(huì)秩序”特性的強(qiáng)調(diào)�,或者說(shuō)將“破壞社會(huì)秩序”的要求融入到對(duì)各種行為類型的解釋中去,也沒(méi)有與各種行為類型相獨(dú)立的并列意義�����。所以,“重大損失”要素并非不能歸入濫用職權(quán)造成的職務(wù)行為公正性受損的結(jié)果中�。論者論證的軌跡是:濫用職權(quán)罪規(guī)定了兩個(gè)相互并列且獨(dú)立的結(jié)果要件,各自對(duì)應(yīng)不同法益���,即“職務(wù)行為的公正性”和“公共利益或個(gè)人權(quán)利”��。本來(lái)����,“重大損失”是不是實(shí)害犯中的實(shí)害結(jié)果或者說(shuō)濫用職權(quán)罪是不是實(shí)害犯���,需要依托該罪法益來(lái)回答�����,即以確立法益助力結(jié)果屬性的判定���;但論者卻從“重大損失”的規(guī)定推出了另一重法益“公共利益或個(gè)人權(quán)利”,“公共利益或個(gè)人權(quán)利”這一法益本來(lái)是要用以判定“重大損失”屬性的�,現(xiàn)在變成了從“重大損失”導(dǎo)出。這便是典型的“法益與構(gòu)成要件解釋”的雙向循環(huán)��,完全看不到所謂法益解釋論機(jī)能的發(fā)揮。這種“要素”與“法益”的“閉循環(huán)”����,不可能甄別出結(jié)果型要素的屬性。
另一種思路是�,由刑法外的其他法規(guī)來(lái)探知法益,再試圖找尋《刑法》相關(guān)個(gè)罪文本的“對(duì)應(yīng)項(xiàng)”��。例如����,對(duì)于騙取貸款罪的法益�����,有學(xué)者采取了如下的探尋路徑:《商業(yè)銀行法》第1條強(qiáng)調(diào)維護(hù)金融秩序�,第82條規(guī)定騙取貸款構(gòu)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(zé)任,這說(shuō)明騙取貸款侵害了貸款秩序�;至于貸款秩序的具體內(nèi)容,要根據(jù)相關(guān)的金融法規(guī)來(lái)確定���?����!顿J款通則》第1條規(guī)定:“為了規(guī)范貸款行為�����,維護(hù)借貸雙方的合法權(quán)益��,保證信貸資產(chǎn)的安全�,提高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,促進(jìn)社會(huì)經(jīng)濟(jì)的持續(xù)發(fā)展����,根據(jù)《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中國(guó)人民銀行法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(guó)商業(yè)銀行法》等有關(guān)法律規(guī)定,制定本通則����。”這就明示了就規(guī)范借款人行為而言�����,貸款秩序表現(xiàn)為“保護(hù)金融機(jī)構(gòu)的合法權(quán)益”“保證信貸資產(chǎn)的安全”“提高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”����,據(jù)此,騙取貸款罪的保護(hù)法益為貸款秩序,具體是金融機(jī)構(gòu)信貸資產(chǎn)的所有權(quán)���、信貸資產(chǎn)的安全���、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。騙取貸款罪規(guī)定中的“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(jī)構(gòu)貸款”“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(jī)構(gòu)造成重大損失”對(duì)應(yīng)于“保護(hù)金融機(jī)構(gòu)的合法權(quán)益”���,“有其他嚴(yán)重情節(jié)”(《刑法修正案(十一)》已經(jīng)刪除了這一規(guī)定)則需要對(duì)應(yīng)于“保證信貸資產(chǎn)的安全”與“提高貸款使用的整體效益”��。這里��,論者直接援引了其他金融法規(guī)的立法目的���?����?墒?���,從其他金融法規(guī)直接說(shuō)明行為的刑事不法,明顯混淆了不同法域的不法�。基于《刑法》的獨(dú)立性品格,為何《刑法》所保護(hù)的貸款秩序要從《商業(yè)銀行法》《貸款通則》導(dǎo)出�����,而不是從刑法文本出發(fā)��?就屬性存疑的“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(jī)構(gòu)造成重大損失”來(lái)說(shuō)�,論者的思路是,《貸款通則》表明了金融機(jī)構(gòu)的合法權(quán)益在貸款秩序之列��,該損失對(duì)應(yīng)的正好是這種合法權(quán)益�,因此屬于法益侵害結(jié)果??墒牵敖鹑跈C(jī)構(gòu)的合法權(quán)益”是由刑法外的金融法規(guī)而來(lái)�����,如何與刑法文本中的“重大損失”形成“對(duì)接”���?換言之��,其他金融法規(guī)所要保護(hù)的���,《刑法》未必也要保護(hù)����;即便刑法文本存在相應(yīng)的表述��,也不代表就是在“保護(hù)”它�,而可能出于其他目的。吊詭的是����,在稍早的論著中,論者已證成“重大損失”不是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�,而是客觀處罰條件,指明騙取貸款行為本身就具有可罰的不法與責(zé)任�����。既然是客觀處罰條件��,自然不涉及不法評(píng)價(jià)��,那又如何與法益勾連�����?后一論著對(duì)“重大損失”定位之所以準(zhǔn)確��,是因?yàn)橹覍?shí)遵循了“從文本出發(fā)到達(dá)構(gòu)成要件這一‘終點(diǎn)’”����。
還有一種思路是,從個(gè)罪既有法益論入手��,選取或證立“似乎”較為妥適的法益論���,再以該法益論指導(dǎo)解釋相應(yīng)的罪名�����。例如����,對(duì)于經(jīng)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修改后的污染環(huán)境罪����,學(xué)界多認(rèn)為既不能采取純粹生態(tài)學(xué)的法益論,也不能僅采取純粹人類中心的法益論����,而應(yīng)采取生態(tài)學(xué)的人類中心的法益論。在這種雙重法益論下��,就不同法益來(lái)說(shuō),污染環(huán)境罪可以呈現(xiàn)結(jié)果犯與行為犯�、抽象危險(xiǎn)犯與實(shí)害犯的不同形態(tài)。采取同樣路徑����,卻有學(xué)者在肯認(rèn)集合法益二元性的基礎(chǔ)上得出了不同的結(jié)論,即“集合法益的落腳點(diǎn)是可以實(shí)現(xiàn)對(duì)個(gè)體法益前置性����、系統(tǒng)性和長(zhǎng)遠(yuǎn)性保護(hù)的超個(gè)體法益,……這種制度性和體系性的集合特征�,大量涉及國(guó)家與社會(huì)基礎(chǔ)體系的超個(gè)體法益具有精神化和抽象化的特質(zhì),具有獨(dú)立存在價(jià)值���,……其是以個(gè)體法益目標(biāo)為支柱���、以精神化和抽象化超個(gè)體法益為延展的雙重體系,是同時(shí)具備目標(biāo)屬性的個(gè)體法益與基礎(chǔ)屬性的超個(gè)體法益的整合性二元結(jié)構(gòu)”��。顯然�,該說(shuō)只是承認(rèn)“二元性”,但不認(rèn)為存有“兩個(gè)法益”�,對(duì)抽象的環(huán)境系統(tǒng)性法益而言�����,污染環(huán)境罪只能是抽象危險(xiǎn)犯,相關(guān)司法解釋中的“結(jié)果”規(guī)定都不可能作為傳統(tǒng)結(jié)果犯的結(jié)果���?����?梢?jiàn)���,即便都是從理論到理論,仍然會(huì)對(duì)集合法益是“多個(gè)”法益還是“單一”法益存有分歧���,在理論層面恐怕很難分出對(duì)錯(cuò)高下��。
當(dāng)然����,在個(gè)人法益犯罪尤其是侵犯人身權(quán)利�、民主權(quán)利犯罪中,較少對(duì)法益內(nèi)容出現(xiàn)爭(zhēng)議�����,甄別某結(jié)果要素是否表達(dá)該法益,相對(duì)較為容易���。例如����,誣告陷害罪�����、侮辱罪�����、誹謗罪�����、侵犯通信自由罪等均以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�、情節(jié)惡劣”為構(gòu)成要件,“引起被害人自殺”屬于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�����、情節(jié)惡劣”的情形之一,對(duì)于這種結(jié)果要素�����,明顯不在各罪法益規(guī)制范圍����,應(yīng)作為結(jié)果型情狀��。
(二)融貫性審查
從刑法體系內(nèi)(從文本出發(fā))���、體系外(從其他法規(guī)或既有法益觀入手)探尋法益的路徑��,有時(shí)難以“確證”法益內(nèi)容��,尤其是難以明確集合法益是否包含個(gè)體法益這一“副法益”�,也就很難甄別主要描述個(gè)體法益侵害的所謂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�����。但法益探尋仍然有積極意義�,是我們進(jìn)行甄別的基礎(chǔ)。在界定個(gè)罪法益時(shí)����,某種法益論要完成自我證成���,必須接受法教義學(xué)的嚴(yán)格檢驗(yàn),即需兼顧融貫性與合目的性的雙重考量�����,確保由特定法益觀所致的構(gòu)成要件解釋及處罰范圍的劃定���,不僅在法教義學(xué)邏輯上是成立的��,在刑事政策上也是合理的��?�?梢员值臋z驗(yàn)思路是:通過(guò)具體罪名所處的章節(jié)確認(rèn)主法益�,探尋文本中是否存在“額外”的侵害要求���,將此要求對(duì)應(yīng)的法益作為“副法益”��,檢驗(yàn)將其作為副法益所致的解釋論即“額外的侵害成為傳統(tǒng)結(jié)果犯的結(jié)果”是否符合融貫性要求�。絕不能認(rèn)為只要在構(gòu)成要件設(shè)定中出現(xiàn)一個(gè)“額外”的結(jié)果要素�����,就直接等同于該罪保護(hù)雙重法益。另外����,在少數(shù)情況下,即使不存在額外的侵害要求��,但某種要素作為傳統(tǒng)結(jié)果犯的結(jié)果明顯存疑���,也應(yīng)加以甄別。如丟失槍支不報(bào)罪中的“嚴(yán)重后果”��,仍然處于“公共安全”法益射程�����,并非額外的一種侵害要求���,但其與“不報(bào)告”之間的因果關(guān)系不明��,也需要甄別�。
“結(jié)果”的規(guī)范意義主要有兩點(diǎn):一是客觀上可歸屬于行為人的行為���;二是在故意犯中作為“明知”與“希望或放任”的對(duì)象�。因此,法教義學(xué)上對(duì)“結(jié)果”要素的甄別應(yīng)主要從這兩點(diǎn)切入�。就前者而言,“著手”概念發(fā)揮著重要作用�。在較長(zhǎng)進(jìn)程的因果流中,必須以“著手”作為“實(shí)行行為”的起始點(diǎn)��,區(qū)別“行為”和“實(shí)行行為”��。犯罪審查的合理模式是:從結(jié)果朝前追溯��,追溯至“著手”點(diǎn)為止����,兩者之間的舉止就是實(shí)行行為。在此基礎(chǔ)上��,再考察結(jié)果是否能在著手時(shí)為行為人所預(yù)見(jiàn)�����,以及是否存在希望或者放任的心理態(tài)度�。要甄別某要素是否描述結(jié)果本身,可以通過(guò)結(jié)果�、行為要素的規(guī)范化實(shí)現(xiàn)��。按照規(guī)范化的理解���,結(jié)果是《刑法》上應(yīng)當(dāng)關(guān)注的結(jié)果,行為必須是“直接”指向法益侵害的行為�����。從擬甄別的“結(jié)果”要素朝前追溯���,判斷能“直接指向”該結(jié)果的行為為何��,再與文本定型化的行為描述進(jìn)行比對(duì),就能判斷該結(jié)果(危險(xiǎn)實(shí)現(xiàn))是否是類型化行為(危險(xiǎn)創(chuàng)設(shè))的“作品”�。不具有條件關(guān)系以及雖有條件關(guān)系但不符合通常結(jié)果歸屬要求的結(jié)果要素,就都是結(jié)果型情狀�����。明確這一點(diǎn)�,對(duì)于故意的認(rèn)定也有重要意義,要求行為人對(duì)沒(méi)有條件關(guān)系的結(jié)果或在實(shí)施預(yù)備行為時(shí)對(duì)實(shí)行行為所導(dǎo)致的結(jié)果具有“明知”“希望或者放任”是不合理的�����。審查的具體路徑便是:結(jié)果(危險(xiǎn)實(shí)現(xiàn))→行為(危險(xiǎn)創(chuàng)設(shè))→因果關(guān)系(合法則的條件關(guān)聯(lián))→結(jié)果歸屬(客觀歸責(zé))→主觀方面(認(rèn)識(shí)與意志)。
以濫用職權(quán)罪為例�。該罪屬于瀆職罪,據(jù)此確認(rèn)“職務(wù)行為的公正性”是其主法益���;除了“濫用職權(quán)”�����,法條又規(guī)定了“致使公共財(cái)產(chǎn)��、國(guó)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”這一“額外”的結(jié)果要素�,由此要素可以“暫時(shí)”析出“公共利益或個(gè)人權(quán)利”這一副法益��;最后從檢驗(yàn)該結(jié)果要素作為傳統(tǒng)結(jié)果犯的結(jié)果是否妥適��?�?梢园l(fā)現(xiàn)�����,一旦將“重大損失”定位為對(duì)“公共利益或個(gè)人權(quán)利”這一副法益的“實(shí)害”從而使濫用職權(quán)罪成為實(shí)害犯��,將導(dǎo)致如下諸多問(wèn)題:(1)根據(jù)相關(guān)司法解釋�,“重大損失”包括“造成死亡1人以上”��,這就意味著濫用職權(quán)行為必須具有故意殺人罪的“實(shí)行行為性”���,但對(duì)于沒(méi)有故意殺人罪的“實(shí)行行為性”的濫用職權(quán)行為,司法實(shí)踐仍然會(huì)將死亡結(jié)果歸屬于濫用職權(quán)行為���;如果不認(rèn)可這樣的司法實(shí)踐�����,必然會(huì)使濫用職權(quán)罪限縮在很小的適用范圍內(nèi)(大多數(shù)濫用職權(quán)行為不具備故意殺人罪的“實(shí)行行為性”)�����,從刑事政策上看也不合理�����。(2)“造成死亡1人以上”既然是實(shí)害結(jié)果,就必然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對(duì)該結(jié)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態(tài)度���,這不僅有違常識(shí)(多數(shù)行為人并無(wú)這種態(tài)度)���,而且導(dǎo)致成罪范圍過(guò)于狹窄��;不僅如此�����,如果對(duì)這種結(jié)果持希望或放任的態(tài)度�,對(duì)應(yīng)“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”的法定刑也不合適�。(3)如果將本罪定位為過(guò)失犯罪,似乎可以避免上述問(wèn)題����,但是,這樣無(wú)法與玩忽職守罪的罪過(guò)形式相協(xié)調(diào)�,也不符合“過(guò)失犯罪,法律有規(guī)定的才負(fù)刑事責(zé)任”的規(guī)定(濫用職權(quán)罪規(guī)定中并無(wú)過(guò)失的文理根據(jù))�。倘若將本罪作為復(fù)合罪過(guò)形式,除了存在前述缺陷外���,也有?!缎谭ā穼⒐室馀c過(guò)失分立的宗旨�。總之��,經(jīng)客觀歸責(zé)檢驗(yàn)���,濫用職權(quán)與“重大損失”通常不具備后者處在前者類型性危險(xiǎn)范圍內(nèi)的歸屬關(guān)系�����;以主觀罪過(guò)檢驗(yàn)����,作為故意犯罪的濫用職權(quán)罪,其意志對(duì)象也不應(yīng)及于“重大損失”���;如果要求濫用職權(quán)必須具有造成重大損失的“實(shí)行行為性”����,故意的意志所及也必須包括重大損失�����,則濫用職權(quán)罪的適用范圍將非常狹窄��,其規(guī)制范圍幾乎與故意殺人罪等相同��,恐失去獨(dú)立為罪的意義����。如此甄別的結(jié)果便是,“重大損失”屬于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�。
同理,《刑法》第148條規(guī)定的生產(chǎn)��、銷售不符合衛(wèi)生標(biāo)準(zhǔn)的化妝品罪中的“造成嚴(yán)重后果”也可被甄別為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��,既不要求行為人對(duì)他人的重傷��、死亡結(jié)果具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意志�����,也不要求行為與重傷�����、死亡結(jié)果之間符合通常的結(jié)果歸屬條件���,否則���,就可以直接認(rèn)定為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。但是�����,通說(shuō)基于文本中是否描述了實(shí)害或具體危險(xiǎn),將第141條規(guī)定的生產(chǎn)�����、銷售假藥罪和第144條規(guī)定的生產(chǎn)����、銷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作為抽象危險(xiǎn)犯�,其他生產(chǎn)、銷售特定偽劣產(chǎn)品的犯罪都是實(shí)害犯或具體危險(xiǎn)犯����。無(wú)論怎樣,“生產(chǎn)���、銷售”是各罪共通的“行為”��,既然在生產(chǎn)����、銷售不符合衛(wèi)生標(biāo)準(zhǔn)的化妝品罪中不能被認(rèn)定為造成所描述“實(shí)害”的“實(shí)行行為”��,在其他各罪中也應(yīng)如此���,通說(shuō)的觀念不足取�����。
又如��,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第46條刪除了《刑法》原第338條第1款中的“向土地�、水體�、大氣”的文字,將“造成重大環(huán)境污染事故�,致使公私財(cái)產(chǎn)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(yán)重后果”修改為“嚴(yán)重污染環(huán)境”。最高人民法院���、最高人民檢察院2016年發(fā)布的《關(guān)于辦理環(huán)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(wèn)題的解釋》第1條規(guī)定了18項(xiàng)“嚴(yán)重污染環(huán)境”的情形����,其中�����,前8項(xiàng)表面上不涉及結(jié)果因素����,只是對(duì)行為特征的描述�����,此時(shí)污染環(huán)境罪好像具有行為犯性質(zhì)���;后9項(xiàng)則表述污染環(huán)境行為所帶來(lái)的各種后果,包括對(duì)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本身的損害和人身���、財(cái)產(chǎn)損失等��,污染環(huán)境罪似乎又可視為結(jié)果犯�����。有學(xué)者認(rèn)為����,就環(huán)境法益而言�,前8種情形屬于行為犯,第10��、12�����、13種情形屬于結(jié)果犯,需要進(jìn)行因果關(guān)系與結(jié)果歸屬的判斷����;就人的生命����、健康等法益來(lái)說(shuō),第9���、11以及第14至第17種情形屬于結(jié)果犯���,也需要進(jìn)行因果關(guān)系與結(jié)果歸屬的判斷。在污染環(huán)境行為造成了嚴(yán)重的環(huán)境污染�����,但未對(duì)人的生命�、健康等造成實(shí)害時(shí),相對(duì)于環(huán)境法益是實(shí)害犯��,相對(duì)于人的法益只是抽象危險(xiǎn)犯�;當(dāng)污染環(huán)境行為不僅對(duì)環(huán)境造成了嚴(yán)重污染����,而且造成了人員傷亡����,則對(duì)兩種法益來(lái)說(shuō),都是實(shí)害犯�。其中結(jié)果犯與實(shí)害犯性質(zhì)的認(rèn)定,可能存在如下疑點(diǎn):(1)混同直接結(jié)果與間接結(jié)果��,忽視只有直接結(jié)果才符合通常的歸屬條件���。誠(chéng)然��,司法解釋列舉的結(jié)果情形或許能通過(guò)與污染環(huán)境行為之間的“條件關(guān)系”認(rèn)定�����,但其中的間接結(jié)果難以通過(guò)客觀歸責(zé)的校驗(yàn)���。環(huán)境污染結(jié)果具有層次性,污染行為先造成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損害的直接后果����,再進(jìn)一步造成人身和財(cái)產(chǎn)損害的間接后果���。由于環(huán)境具有流動(dòng)性和有限再生性的特性,即便遭受損害�,也不一定導(dǎo)致人身財(cái)產(chǎn)損害,兩種損害是先后層面而非并列關(guān)系��,環(huán)境的嚴(yán)重?fù)p害才是“嚴(yán)重污染環(huán)境”的直接和核心要素�。導(dǎo)致間接結(jié)果出現(xiàn)的因果流程非常復(fù)雜而且往往歷時(shí)很久�,不能由行為人直接操控,污染行為只是制造了機(jī)會(huì)而已��。在間接結(jié)果表現(xiàn)為人員傷亡的場(chǎng)合����,如果污染行為直接支配了導(dǎo)致傷亡的因果流程,行為人就應(yīng)成立不法程度更高的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�����。一言以蔽之�,對(duì)于間接結(jié)果,污染行為只具有“潛在的危險(xiǎn)”��,不足以認(rèn)定“實(shí)行行為性”�����。(2)導(dǎo)致罪刑不相適應(yīng)。第17項(xiàng)規(guī)定的后果包含“致使1人以上重傷”�����,其對(duì)應(yīng)的法定刑只是“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�����,并處或者單處罰金”��,明顯低于故意傷害致人重傷“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”的法定刑����。(3)污染行為時(shí)點(diǎn)的故意難以認(rèn)定。對(duì)于人身����、財(cái)產(chǎn)損害的間接結(jié)果,難以認(rèn)定行為人具有故意����。如第14項(xiàng)列舉的“致使疏散、轉(zhuǎn)移群眾5000人以上”����,如何證明行為人在實(shí)施污染行為時(shí)對(duì)此后果具有明知且持希望或者放任態(tài)度�?可以設(shè)想的是�����,基于環(huán)境污染的緩慢進(jìn)程��,疏散��、轉(zhuǎn)移群眾完全可能是在實(shí)施污染行為后很長(zhǎng)時(shí)間(如數(shù)年甚至更長(zhǎng))進(jìn)行����,行為人對(duì)其如何預(yù)見(jiàn)���?綜上���,污染環(huán)境罪中的“嚴(yán)重污染環(huán)境”也是一種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。
甄別結(jié)果型情狀的過(guò)程充分表明���,認(rèn)為“抽象危險(xiǎn)犯既保護(hù)具體的個(gè)人法益�����,也保護(hù)抽象的集體法益��;前置性的集體法益是‘阻擋層法益’����,后置的個(gè)人法益是‘背后層法益’”的觀點(diǎn)存在片面性。在立法論上����,立法者確實(shí)是以保護(hù)個(gè)人法益為目的設(shè)置抽象危險(xiǎn)犯,集體法益的出發(fā)點(diǎn)是保護(hù)個(gè)人法益����。但是,一旦立法完成�,集體法益就具有受專門保護(hù)的超個(gè)體實(shí)存地位,個(gè)人法益保護(hù)的目的已經(jīng)“融合”在集體法益中����,不再具有實(shí)存地位。正因?yàn)槿绱?�,個(gè)人法益才是“背后層”法益�����,它是到不了“前臺(tái)”來(lái)的。在解釋論上�,個(gè)人法益對(duì)應(yīng)的“結(jié)果”經(jīng)法教義學(xué)檢驗(yàn),只能是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����,而結(jié)果型情狀的存在目的,不在于表達(dá)特定法益的侵害結(jié)果���,不能據(jù)此直接導(dǎo)出所謂保護(hù)法益��。
三��、作為抽象危險(xiǎn)判斷“中間項(xiàng)”的結(jié)果型情狀
(一)抽象危險(xiǎn)的結(jié)果屬性
從“原始”犯罪既遂是指“實(shí)現(xiàn)利益侵害結(jié)果的行為”的概念內(nèi)涵出發(fā)�����,出于法律適用效益的觀點(diǎn),才必須以個(gè)別條文解釋的類型樣態(tài)�,區(qū)分行為犯與結(jié)果犯。區(qū)分行為犯與結(jié)果犯的重要實(shí)益在于����,有無(wú)判斷因果關(guān)系的必要。行為犯的構(gòu)成僅以一定的行為為要件,而不以侵害結(jié)果的實(shí)現(xiàn)為要件�����,也就無(wú)需檢驗(yàn)具體事實(shí)中是否有侵害結(jié)果的實(shí)現(xiàn)�,當(dāng)然更沒(méi)有行為與結(jié)果之間因果關(guān)系的認(rèn)定問(wèn)題,例如重婚罪只要有重婚行為就可以成罪�����。和行為犯相對(duì)應(yīng)的結(jié)果犯除了以一定的行為為要件外�,還以侵害結(jié)果的實(shí)現(xiàn)為要件,既要檢驗(yàn)個(gè)案中侵害結(jié)果是否實(shí)現(xiàn)��,犯罪既遂也以行為和結(jié)果之間具有因果關(guān)系為要件����,例如故意殺人罪除了殺人行為外,還以被害人死亡結(jié)果為要件�,既遂要求死亡結(jié)果可歸屬于殺人行為。與此同時(shí)����,通說(shuō)認(rèn)為抽象危險(xiǎn)是行為的危險(xiǎn),具體危險(xiǎn)才是結(jié)果危險(xiǎn)��,因此具體危險(xiǎn)犯屬于結(jié)果犯,抽象危險(xiǎn)犯屬于行為犯��,分屬兩個(gè)不同的概念范疇�����。
事實(shí)上����,犯罪分類的意義在于通過(guò)分類來(lái)呈現(xiàn)各罪構(gòu)成要件該當(dāng)性所應(yīng)具備的不同判斷要素。將抽象危險(xiǎn)犯定位為行為犯��,牽涉到對(duì)于“結(jié)果”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犯罪分類的目的選擇����。如果以行為造成法益危險(xiǎn)的“結(jié)果無(wú)價(jià)值”的侵害或危險(xiǎn)的“狀態(tài)”作為解釋對(duì)象,危險(xiǎn)犯所呈現(xiàn)行為對(duì)于法益危險(xiǎn)的要求����,不能排除也是“結(jié)果”的一種可能解釋。因此�����,在使用“結(jié)果”的文義符號(hào)時(shí)���,要掌握究竟我們要表達(dá)的是包含法益侵害實(shí)害與法益危險(xiǎn)狀態(tài)的廣義結(jié)果����,還是強(qiáng)調(diào)與行為有時(shí)空分離��、必須檢驗(yàn)與行為是否有因果關(guān)系的狹義結(jié)果���。實(shí)害犯與危險(xiǎn)犯的區(qū)分標(biāo)準(zhǔn)在于是否造成法益的實(shí)際侵害���,主要是為了進(jìn)一步判斷行為是否造成法益的實(shí)害才能認(rèn)定既遂;與區(qū)分行為犯與結(jié)果犯是為了強(qiáng)調(diào)因果關(guān)系的檢驗(yàn)才能判定既遂明顯不同�����。因此���,沒(méi)有必要將兩種分類摻雜在一起���,進(jìn)而刻意強(qiáng)調(diào)抽象危險(xiǎn)犯一定是行為犯。抽象危險(xiǎn)犯也必須存在有危險(xiǎn)狀態(tài)的危險(xiǎn)結(jié)果���,與實(shí)害���、具體危險(xiǎn)犯同屬結(jié)果犯的下位類型���。
只有人的行為才能引發(fā)有意義的行為法益侵害流程,也才是規(guī)范禁止的對(duì)象���,這固然是理解“不法”正確的出發(fā)點(diǎn)��,然而�����,如果不考量特定因果歷程的發(fā)展?fàn)顟B(tài)����,只是單從行為時(shí)點(diǎn)考量是否應(yīng)予禁止�����,實(shí)際上完全無(wú)法確認(rèn)什么是《刑法》所應(yīng)禁止的行為模式�。一個(gè)行為之所以應(yīng)予禁止的原始理由,正是該行為于“后續(xù)因果流程”的利益侵害作用����,只有當(dāng)特定行為有可能造成法益侵害時(shí)���,《刑法》對(duì)該行為的禁止才具備正當(dāng)性���?���;蛘哒f(shuō)����,只有經(jīng)由解釋、演繹出行為有可能產(chǎn)生的后續(xù)作用���,視其后續(xù)作用的強(qiáng)弱����,再?zèng)Q定是否將該行為納入禁止之列����,即由“結(jié)果發(fā)生”回溯行為的不法性。如果現(xiàn)實(shí)上不存在一個(gè)具體可得感知的“結(jié)果”�����,也就形同在規(guī)范上欠缺一個(gè)行為人應(yīng)受處罰的理由,因?yàn)榭陀^上不可能回溯確認(rèn)行為人是否實(shí)施了一個(gè)《刑法》上所禁止的行為��。在這一意義上�����,可以說(shuō)犯罪是引起結(jié)果的行為類型����,結(jié)果是所有犯罪共通的構(gòu)成要件要素,犯罪全部都是結(jié)果犯��。
這樣看來(lái)�,所謂具體危險(xiǎn)犯是指條文中“明文規(guī)定必須發(fā)生某種危險(xiǎn)才能成立犯罪”的說(shuō)法有失偏頗。是否寫有“危險(xiǎn)”字樣�,充其量不過(guò)是具體危險(xiǎn)犯的形式意義,即便沒(méi)有“危險(xiǎn)”字樣�����,也可能是具體危險(xiǎn)犯��。具體危險(xiǎn)的實(shí)質(zhì)意義在于����,必須要在個(gè)案中判斷行為確實(shí)導(dǎo)致了法益的具體危險(xiǎn)狀態(tài)����,即“行為的客體在具體案件中真實(shí)地處于危險(xiǎn)之中���,也就是說(shuō),結(jié)果的不發(fā)生僅僅是偶然的”��。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為例�,其法益公認(rèn)為“不特定或者多數(shù)人的生命、身體及財(cái)產(chǎn)安全”��,具體危險(xiǎn)意味著不但必須有不特定或者多數(shù)人進(jìn)入行為的作用領(lǐng)域�,同時(shí)其生命、身體及財(cái)產(chǎn)安全面臨現(xiàn)實(shí)上直接而緊迫���、隨時(shí)可能發(fā)生實(shí)害的狀態(tài)�����。不同的是�,抽象危險(xiǎn)犯不要求所謂相應(yīng)對(duì)象進(jìn)入行為的射程范圍���,也不要求時(shí)間上的緊迫性�����。換言之���,抽象危險(xiǎn)犯無(wú)法以正面定義(不能說(shuō)明何為“抽象”危險(xiǎn))���,只能以負(fù)面解釋(不是具體危險(xiǎn)的就是抽象危險(xiǎn))。因此�����,抽象危險(xiǎn)犯與具體危險(xiǎn)犯一樣��,也是“結(jié)果危險(xiǎn)”的犯罪���,而不是所謂“行為危險(xiǎn)”的犯罪�。
(二)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功能
如所周知���,在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追求風(fēng)險(xiǎn)管控的潮流下�,抽象危險(xiǎn)犯成為分配社會(huì)風(fēng)險(xiǎn)的最佳立法手段�����,甚至是保護(hù)超個(gè)人法益所采取的主要立法模式。因應(yīng)嚴(yán)重且難以預(yù)測(cè)的社會(huì)風(fēng)險(xiǎn)����,盡可能提前預(yù)防危險(xiǎn)行為向?qū)嵑Φ霓D(zhuǎn)化,故而將法益抽象化和保護(hù)前置化�����。將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不法評(píng)價(jià)重心置于“行為本身所具有的危險(xiǎn)性”���,就是這種“前置保護(hù)”功能的體現(xiàn),但這僅是抽象危險(xiǎn)犯功能之一����。
由于風(fēng)險(xiǎn)社會(huì)情勢(shì)下風(fēng)險(xiǎn)的高發(fā)性和不確定性,使得實(shí)害發(fā)生的因果流程難以識(shí)別和確認(rèn)��;另外���,風(fēng)險(xiǎn)社會(huì)中形成實(shí)害的風(fēng)險(xiǎn)作用機(jī)制錯(cuò)綜復(fù)雜���,導(dǎo)致難以將實(shí)害結(jié)果具體歸責(zé)于特定行為人。無(wú)論是實(shí)害犯還是具體危險(xiǎn)犯,都無(wú)法避免因果關(guān)系和歸責(zé)上的難題����,只能采取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立法方式。以環(huán)境犯罪為例�����,基于實(shí)害結(jié)果的不確定性以及因果關(guān)系的難以預(yù)測(cè)性�,“累積性”的思考方式就為“行為與法益之間的實(shí)質(zhì)對(duì)應(yīng)關(guān)系”(任何犯罪都必須具備)提供了一定的連接性,作為這種對(duì)應(yīng)關(guān)系的基礎(chǔ)����。一方面,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破壞體現(xiàn)出典型的“行為共害”特征����,個(gè)別污染行為往往難以構(gòu)成對(duì)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的整體破壞,但多人多次污染行為漸次累積起來(lái)則會(huì)導(dǎo)致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的嚴(yán)重破壞�,故對(duì)單個(gè)污染行為也有預(yù)防必要;另一方面��,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的復(fù)雜性決定了侵害程度����、過(guò)程或因果關(guān)系難以把握而使法益侵害體現(xiàn)出一定的偶然性���,某種污染行為的侵害后果可能要經(jīng)歷代際更迭才能體現(xiàn),因而必須提前到法益風(fēng)險(xiǎn)產(chǎn)生的初始階段就加以預(yù)防����。認(rèn)為污染環(huán)境罪“既可能是行為犯也可能是結(jié)果犯,也可能是危險(xiǎn)犯與實(shí)害犯”的觀點(diǎn)存在疑問(wèn)����。
另外,超個(gè)人法益往往具有集合性���、抽象性和精神化的特點(diǎn)����,無(wú)法進(jìn)行實(shí)害描述���,不存在所謂實(shí)害判斷的邏輯問(wèn)題。這類法益主要用來(lái)保護(hù)全局性和系統(tǒng)性的�、難以通過(guò)實(shí)存客體加以保護(hù)的整體安全和秩序,無(wú)法對(duì)應(yīng)侵害的實(shí)體對(duì)象���,也不能直接還原為具體個(gè)人法益�����。由于不能表達(dá)為依靠作用對(duì)象實(shí)際狀態(tài)判斷的實(shí)害或具體危險(xiǎn)�����,只能采取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規(guī)范形式��。例如���,一般認(rèn)為偽證罪的法益為司法活動(dòng)的公正性��,但怎樣的損害算是對(duì)“公正性”的實(shí)害����,立法者難以描述�����,如果不能把握何為“實(shí)害”����,也就無(wú)從判斷何為“具體危險(xiǎn)”,因此��,對(duì)“司法活動(dòng)的公正性”這種精神化法益,唯一可行的立法方式就是抽象危險(xiǎn)犯�。
問(wèn)題是,是否只有采取“僅描述行為”方式的抽象危險(xiǎn)犯立法�����,才能實(shí)現(xiàn)上述功能���?答案顯然是否定的����。前已述及��,抽象危險(xiǎn)只能從負(fù)面定義���,只要立法表述不觸及“實(shí)害”與“具體危險(xiǎn)”即可���,這就為存在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的規(guī)定提供了解釋空間�����,也就是在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框架下理解這種要素的屬性�����。
(三)作為抽象危險(xiǎn)判斷“中間項(xiàng)”的情狀
1.抽象危險(xiǎn)判斷的特殊性
立法者將對(duì)外表征出法益侵害的“損害狀態(tài)”內(nèi)化于不法構(gòu)成要件的結(jié)果要素,綜合結(jié)果����、損害與法益侵害三者的對(duì)應(yīng)關(guān)系,分則各罪的設(shè)立原型即以所謂“結(jié)果刑法”為典范��,特別是指實(shí)害犯的類型�。立法者對(duì)實(shí)害犯的不法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所進(jìn)行的文字描述,在意義上提出直接等同于法益侵害�,即“法益侵害結(jié)果”。與實(shí)害犯同質(zhì)���,具體危險(xiǎn)犯中對(duì)具體危險(xiǎn)的文字描述�����,也被等同于法益危險(xiǎn)��,即“法益危險(xiǎn)結(jié)果”�?���;蛘?�,實(shí)害犯與具體危險(xiǎn)犯中的有關(guān)文字描述��,都是針對(duì)“結(jié)果本身”�。
抽象危險(xiǎn)犯則有所不同����。危險(xiǎn)是“法益侵害的可能性”,以保護(hù)法益的直接關(guān)聯(lián)性為前提�����,即“直接的危險(xiǎn)”����。如果只是“某種事態(tài)發(fā)生的可能性”,嚴(yán)格來(lái)說(shuō)尚不能稱為危險(xiǎn)����。抽象危險(xiǎn)其實(shí)是通過(guò)經(jīng)驗(yàn)上想定的“其他事態(tài)”發(fā)生可能性來(lái)間接判斷保護(hù)法益的危險(xiǎn)。這個(gè)“其他事態(tài)”就成為介于行為與法益之間��,判斷法益侵害可能性的“中間項(xiàng)”���。因此�����,抽象危險(xiǎn)犯始終保有結(jié)果要素����,只不過(guò)這種要素承繼了結(jié)果原有的“表征侵害現(xiàn)實(shí)”的功能����,結(jié)合特定關(guān)聯(lián)對(duì)象于外部世界的自然性或社會(huì)性變化,轉(zhuǎn)化為“已創(chuàng)成危險(xiǎn)的特殊事件”�����,這種“中間結(jié)果”作為法益危險(xiǎn)的間接證明�����?�!敖Y(jié)果型情狀要素”正好能起到這樣的作用����。“危險(xiǎn)行為+結(jié)果型情狀”的結(jié)構(gòu)生成了“兩步法”歸責(zé):第一步是危險(xiǎn)行為與結(jié)果型情狀是否具有因果關(guān)系(采取條件說(shuō)),如果答案為肯定��,表明該情狀可歸責(zé)于行為人���;第二步是結(jié)果型情狀表征的危險(xiǎn)狀態(tài)與抽象危險(xiǎn)結(jié)果之間是否具有客觀上的歸責(zé)關(guān)聯(lián)�。只不過(guò)����,因?yàn)槌橄笪kU(xiǎn)結(jié)果的難以把握,立法者才運(yùn)用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作為判斷的“中間項(xiàng)”��,因此第二步的歸責(zé)關(guān)聯(lián)是立法擬制的���,實(shí)務(wù)中無(wú)需檢驗(yàn)�。這種歸責(zé)模式的實(shí)益在于:一方面通過(guò)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展現(xiàn)了危險(xiǎn)結(jié)果必須存在��,才可以判斷為犯罪既遂���,實(shí)現(xiàn)限縮刑罰擴(kuò)張的目的�;另一方面也利用抽象危險(xiǎn)犯行為與危險(xiǎn)狀態(tài)的因果關(guān)聯(lián)不需要積極證明的立法選擇�,解決個(gè)案證明具體因果關(guān)聯(lián)的困境。
總之���,對(duì)于侵害測(cè)定困難的法益來(lái)說(shuō)���,實(shí)害犯與具體危險(xiǎn)犯根本就是不能采取的立法模式;至于侵害測(cè)定可能的法益��,結(jié)果型情狀與“侵害對(duì)象進(jìn)入行為的射程范圍�����、侵害發(fā)生時(shí)間上的緊迫性”的具體危險(xiǎn)無(wú)涉����,仍是判斷抽象危險(xiǎn)的中間項(xiàng)。
2.“中間項(xiàng)”的功能展開(kāi)
就“侵害測(cè)定困難的法益”�,以尋釁滋事罪為例說(shuō)明。該罪規(guī)定的行為類型中����,除了“在公共場(chǎng)所起哄鬧事”有“造成公共場(chǎng)所秩序嚴(yán)重混亂”的結(jié)果描述之外,其他幾種行為都采用了“情節(jié)惡劣”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的情節(jié)犯模式��。相關(guān)司法解釋在對(duì)“情節(jié)惡劣”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進(jìn)行列舉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既有“致1人以上輕傷或者2人以上輕微傷”的“實(shí)害結(jié)果”標(biāo)準(zhǔn),也有“多次”“持兇器”等行為屬性標(biāo)準(zhǔn)����。那么,能否據(jù)此認(rèn)為尋釁滋事罪既是實(shí)害犯又是行為犯�����?答案是否定的�。尋釁滋事罪的法益為抽象的公共秩序,具有抽象性和精神化的特質(zhì)�,難以測(cè)定法益受到“怎樣”及“何種程度”的侵害,“致1人以上輕傷或者2人以上輕微傷”的結(jié)果只是局部可查的擾亂公共秩序的要素����,并不是直接描述對(duì)整體公共秩序這一法益本身的侵害。因此�����,相關(guān)司法解釋中對(duì)“情節(jié)惡劣”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列舉的結(jié)果都是情狀要素�����,是判斷“造成公共秩序混亂”這一抽象危險(xiǎn)的“中間項(xiàng)”���。即便是對(duì)“在公共場(chǎng)所起哄鬧事”行為類型立法上有“造成公共場(chǎng)所秩序嚴(yán)重混亂”的“結(jié)果”描述���,也只能將其理解為抽象危險(xiǎn)����。
就“侵害測(cè)定可能的法益”��,以危險(xiǎn)駕駛罪中的“醉駕”為例說(shuō)明���。作為危險(xiǎn)駕駛罪法益的“公共安全”內(nèi)容為不特定或者多數(shù)人的生命、身體及財(cái)產(chǎn)安全�,這是一種可以具象化描述的法益,實(shí)害犯��、具體危險(xiǎn)犯�、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立法模式都能選擇。如果選取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立法方式����,所要求的是一種對(duì)法益的“潛在”危險(xiǎn)而不是“具體”危險(xiǎn),從而區(qū)別于具體危險(xiǎn)犯�。也就是說(shuō),現(xiàn)實(shí)上不需要有法益承載對(duì)象進(jìn)入行為影響領(lǐng)域����,也無(wú)需要求時(shí)間上的緊迫性�。但這不代表抽象危險(xiǎn)的判斷只能存在于行為時(shí)��,行為后也有判斷危險(xiǎn)性的空間����。像是德國(guó)刑法第325條空氣污染罪“有損害他人健康、動(dòng)物植物或其他重大價(jià)值之物之虞的大氣變化”的規(guī)定�����,就是一種特殊的“行為后狀態(tài)的危險(xiǎn)性”�����,但仍是一種“一般性”的判斷��,不需要有具體的保護(hù)對(duì)象進(jìn)入行為影響領(lǐng)域及時(shí)間上的緊迫性�����。在我國(guó)����,作為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醉駕立法本無(wú)需考量具體危險(xiǎn)的有無(wú)���,但司法實(shí)踐企圖通過(guò)對(duì)具體危險(xiǎn)的現(xiàn)實(shí)考量限縮處罰范圍,這就抵牾了立法隱含的擴(kuò)張性處罰的規(guī)范目的�,從而存在將該罪歸之于具體危險(xiǎn)犯的嫌疑,學(xué)界也陷入了能否“反證”不存在現(xiàn)實(shí)危險(xiǎn)的無(wú)休止的爭(zhēng)論��。對(duì)此�����,需要厘清其中何為“具體危險(xiǎn)”���、何為“抽象危險(xiǎn)”。人們經(jīng)常說(shuō)�����,在空無(wú)一人的廣闊地帶醉駕����,不會(huì)發(fā)生對(duì)任何人的危險(xiǎn)。其中的“危險(xiǎn)”判斷���,已經(jīng)在考察“有沒(méi)有人進(jìn)入醉駕領(lǐng)域”了��,顯然是一種具體危險(xiǎn)�。更為重要的是,“空無(wú)一人的廣闊地帶”是否經(jīng)過(guò)排查�����,經(jīng)過(guò)了怎樣的排查��?“通過(guò)一次可靠的排查以排除任何危險(xiǎn)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”���,“如果有誰(shuí)贊成在排除任何危險(xiǎn)時(shí)進(jìn)行目的性限縮��,那就使得……抽象危險(xiǎn)型犯罪不再是抽象危險(xiǎn)性犯罪��,而成為具體危險(xiǎn)型犯罪了”��。對(duì)抽象危險(xiǎn)犯進(jìn)行“具體危險(xiǎn)”的目的性限縮解釋�,從方法論上就是錯(cuò)誤的����。但是,對(duì)“抽象危險(xiǎn)”加以限縮是完全正當(dāng)?shù)?。人們似乎已?jīng)習(xí)慣以“血液酒精含量”為標(biāo)準(zhǔn)“一刀切”地認(rèn)定“醉酒”,可是�,超過(guò)這一酒精含量的人可能駕駛能力并未下降���,沒(méi)有達(dá)到這一酒精含量的人也可能駕駛能力已經(jīng)下降。因此��,所謂抽象危險(xiǎn)并非通過(guò)“血液酒精含量”來(lái)簡(jiǎn)單認(rèn)定�����,而是有賴于行為人是否有能力安全駕駛�����,“不能安全駕駛”的狀態(tài)才是判斷重點(diǎn)����?���!把壕凭俊笔且姥绦蛞饬x上的經(jīng)驗(yàn)法則所建構(gòu)的具體化標(biāo)準(zhǔn),同時(shí)作為一種帶有間接證明效果的事實(shí)基礎(chǔ)����,是證明能否安全駕駛的證據(jù)方法之一,是“醉酒”的標(biāo)準(zhǔn)而非“不能安全駕駛”的唯一標(biāo)準(zhǔn)��。因此,有必要借助不成文的“不能安全駕駛”這一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���,作為判斷醉駕所致抽象危險(xiǎn)的“中間項(xiàng)”��,以此實(shí)現(xiàn)對(duì)抽象危險(xiǎn)的限縮解釋�����。需要明確的是��,“不能安全駕駛”雖然表征了醉駕行為的危險(xiǎn)性�����,但這種危險(xiǎn)性相對(duì)于公共安全仍是一種“潛在的危險(xiǎn)性”��,即抽象危險(xiǎn)而不是具體危險(xiǎn)����。
3.對(duì)“中間項(xiàng)”的主觀要求
對(duì)作為“中間項(xiàng)”的結(jié)果型情狀的主觀要求�,取決于其定位。現(xiàn)有的各類解決方案��,無(wú)論是客觀的超過(guò)要素說(shuō)、罪量要素∕客觀處罰條件說(shuō)�����、主要罪過(guò)說(shuō)��,還是故意的要素分析模式說(shuō)�����,本質(zhì)上都是通過(guò)放寬故意的成立標(biāo)準(zhǔn)��,倡導(dǎo)多元化的故意類型�����。但故意的標(biāo)準(zhǔn)調(diào)整不僅影響故意認(rèn)定�����,故意犯的構(gòu)造更具有整體性�,每個(gè)要件都具有牽一發(fā)而動(dòng)全身的特點(diǎn)��,無(wú)法隨意對(duì)某一要件進(jìn)行改動(dòng)��。例如,客觀的超過(guò)要素說(shuō)雖正確把握了這種要素與普通構(gòu)成要件結(jié)果要素的不同���,卻認(rèn)為對(duì)該種要素不要求行為人認(rèn)識(shí)(但應(yīng)有認(rèn)識(shí)可能性)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?墒?�,即便是“超過(guò)”的要素���,但依然是客觀的不法要素�,既然如此�����,又怎能在故意的認(rèn)識(shí)之外�����?一方面不要求行為人現(xiàn)實(shí)上認(rèn)識(shí)���;另一方面又讓行為人承擔(dān)故意犯的責(zé)任��,這顯然是自相矛盾�。在本文看來(lái),與抽象危險(xiǎn)犯也是結(jié)果犯對(duì)應(yīng)�����,故意的抽象危險(xiǎn)犯中“明知”與“希望或者放任”的對(duì)象都是抽象危險(xiǎn)這一結(jié)果���,作為判斷這一結(jié)果“中間項(xiàng)”的結(jié)果型情狀并非結(jié)果本身�,自然不能理解為《刑法》第15條第1款故意犯罪定義中的“危害社會(huì)的結(jié)果”����。但是,作為與行為具有因果關(guān)聯(lián)的后果����,結(jié)果型情狀仍是不法要素,既然如此�����,就不可能脫逸于故意的認(rèn)識(shí)范圍�����。這種情況下的主觀構(gòu)造便是: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(huì)發(fā)生某種抽象危險(xiǎn)結(jié)果��,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(jié)果發(fā)生�,結(jié)果型情狀作為一種特定化的不法要素,只是要求行為人認(rèn)識(shí)到�,無(wú)需對(duì)其具有希望或者放任態(tài)度。
至此�,本文都是在“故意犯”的范圍內(nèi)討論所謂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。存在的疑問(wèn)是:前文所述是否也可適用于過(guò)失犯�����?或者說(shuō)�,能否承認(rèn)所謂過(guò)失的抽象危險(xiǎn)犯?如在濫用職權(quán)罪中�����,一些濫用職權(quán)行為雖然導(dǎo)致了他人死亡的結(jié)果�,但行為可能不具有故意殺人罪的“實(shí)行行為性”,行為人對(duì)死亡結(jié)果也并無(wú)希望或者放任態(tài)度�����,但司法實(shí)踐依然會(huì)將死亡結(jié)果歸屬于濫用職權(quán)行為。這表明�,“死亡結(jié)果”只是判斷“使職務(wù)行為公正性受損的抽象危險(xiǎn)”的“中間項(xiàng)”,該罪的“重大損失”就應(yīng)被作為一種結(jié)果型情狀�����。問(wèn)題是�����,在玩忽職守罪中�����,“重大損失”是否也是如此定位�?就成立過(guò)失犯所要求的“法益侵害結(jié)果”來(lái)說(shuō),使職務(wù)公正性受損的抽象危險(xiǎn)本身就是“法益侵害結(jié)果”��,這一結(jié)果通過(guò)實(shí)定法“重大損失”的情狀得以間接體現(xiàn)��。但就成立過(guò)失犯所要求的“實(shí)行行為”而言���,《刑法》往往并沒(méi)有嚴(yán)格規(guī)定��,在定型上顯然比故意犯要緩和得多���,這就導(dǎo)致在故意犯中難以成為“實(shí)行行為”的情形��,在過(guò)失犯中可能具有“實(shí)行行為性”���。故而����,在濫用職權(quán)罪不能成為“實(shí)行行為”的,在玩忽職守罪中就可能具有“實(shí)行行為性”����。基于“玩忽職守”實(shí)行行為的緩和性�,通過(guò)由“結(jié)果”回溯考察“著手”的法教義學(xué)檢驗(yàn),可能難以否認(rèn)行為與結(jié)果之間的“直接指向性”���,似乎沒(méi)有必要將“重大損失”作為“中間項(xiàng)”����,而應(yīng)直接作為“最終項(xiàng)”的結(jié)果�。但是,其一����,在過(guò)失犯中����,實(shí)行行為也必須具有導(dǎo)致結(jié)果發(fā)生的“緊迫”危險(xiǎn)���,即使其定型性比故意犯緩和���,但仍然需要具體判斷有無(wú)“緊迫性”,因此����,認(rèn)為過(guò)失犯中行為與結(jié)果之間都具有“直接指向性”顯然以偏概全;其二�����,既然濫用職權(quán)罪是與之對(duì)應(yīng)的故意犯罪��,“職務(wù)行為的公正性”是二者共同的法益���,在濫用職權(quán)罪采取“抽象危險(xiǎn)行為+結(jié)果型情狀”的立法結(jié)構(gòu)�、定位為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情況下���,不能認(rèn)為玩忽職守罪是針對(duì)“重大損失”體現(xiàn)的所謂“公共利益或個(gè)人權(quán)利”法益的實(shí)害犯���。
四���、作為抽象危險(xiǎn)犯“處罰條件”的結(jié)果型情狀
(一)作為“處罰條件”的適例
1.丟失槍支不報(bào)罪中的“嚴(yán)重后果”
《刑法》第129條規(guī)定:“依法配備公務(wù)用槍的人員,丟失槍支不及時(shí)報(bào)告���,造成嚴(yán)重后果的,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��?!眮G失槍支不及時(shí)報(bào)告,只有造成嚴(yán)重后果的�,才成立丟失槍支不報(bào)罪。關(guān)于“嚴(yán)重后果”的性質(zhì)��,學(xué)界存在較大分歧����。有學(xué)者認(rèn)為,不及時(shí)報(bào)告并不一定是造成嚴(yán)重后果的原因����,和造成嚴(yán)重后果之間有因果關(guān)系的是“丟失槍支”的行為��,而不是“不及時(shí)報(bào)告”的行為�。本罪之所以受到處罰�,是因?yàn)閬G失槍支后應(yīng)當(dāng)及時(shí)報(bào)告而沒(méi)有及時(shí)報(bào)告。據(jù)此�����,“嚴(yán)重后果”依然是本罪的“實(shí)害結(jié)果”��,只不過(guò)其原因行為是“丟失槍支”���,顯然��,這是將“丟失槍支”和“不及時(shí)報(bào)告”都作為本罪的行為看待����,只要二者之一與“嚴(yán)重后果”具有因果關(guān)系即可�。但是,該觀點(diǎn)又承認(rèn)本罪的處罰對(duì)象是“不及時(shí)報(bào)告”行為���,既然如此��,舍去作為關(guān)鍵行為的“不及時(shí)報(bào)告”而以只是本罪成立“前提條件”的“丟失槍支”去認(rèn)定因果關(guān)系��,不得不說(shuō)是有疑問(wèn)的��。有學(xué)者認(rèn)為���,“嚴(yán)重后果”雖然是構(gòu)成要件客觀方面的要素�,但必須和“典型的違法要素”相區(qū)別�����,屬于“內(nèi)在的客觀處罰條件”��。一方面��,內(nèi)在的客觀處罰條件使得先前“不及時(shí)報(bào)告”的危險(xiǎn)增大到了可罰的程度��,對(duì)違法性有所影響����;另一方面該條件是否能夠出現(xiàn)���,取決于很多偶然因素�����,雖然要求行為人存在認(rèn)識(shí)���,但只需要存在“極有可能發(fā)生”的高度模糊性認(rèn)識(shí)即可���。這一觀點(diǎn)看到了“嚴(yán)重后果”不是典型的結(jié)果要素,這一點(diǎn)值得肯定��。但是���,其一����,“對(duì)違法性有所影響”的結(jié)果要素有賴于其對(duì)行為的歸屬�����,因果關(guān)系的證立必不可少�����;其二�,“極有可能發(fā)生的高度模糊性認(rèn)識(shí)”所指為何����,實(shí)務(wù)如何操作��?恐怕都有待明確�。還有學(xué)者提出,“嚴(yán)重后果”雖然是構(gòu)成要件要素�����,但只是為了控制處罰范圍�����,不需要行為人對(duì)之具有認(rèn)識(shí)與希望或者放任態(tài)度�����,基于“超出了故意內(nèi)容”這一點(diǎn)��,屬于“客觀的超過(guò)要素”�?����?墒牵热皇恰翱陀^的超過(guò)要素”�,就依然是客觀的、影響違法性的要素���,它就不屬于客觀的“超過(guò)”要素��。此外��,為何原則上客觀要素需要認(rèn)識(shí)到�����,少數(shù)情況下又不需要認(rèn)識(shí)到而只需要有認(rèn)識(shí)可能性��?也缺乏必要的證明�����。實(shí)際上���,即使及時(shí)報(bào)告,也不一定能阻止嚴(yán)重后果發(fā)生�,不及時(shí)報(bào)告與嚴(yán)重后果之間不存在條件關(guān)系,“嚴(yán)重后果”并非不法要素�����,只是單純限制處罰的結(jié)果型情狀。
2.騙取貸款罪中的“重大損失”
《刑法》原第175條第1款規(guī)定:“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(jī)構(gòu)貸款����,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(jī)構(gòu)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(yán)重情節(jié)的,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�,并處或者單處罰金?����!?實(shí)踐中對(duì)“其他嚴(yán)重情節(jié)”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���,使入罪范圍過(guò)寬�����。鑒于此���,《刑法修正案(十一)》第11條刪除了“或者有其他嚴(yán)重情節(jié)”的規(guī)定,僅處罰以欺騙手段獲取貸款��,給金融機(jī)構(gòu)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����。在實(shí)務(wù)中如何正確把握“給金融機(jī)構(gòu)造成重大損失”的含義,就是較為緊要的問(wèn)題����。
有學(xué)者指出,認(rèn)定金融機(jī)構(gòu)的重大損失以被告人實(shí)施欺騙行為為前提�,即只能在與被告人的欺騙行為相關(guān)聯(lián)的意義上理解金融機(jī)構(gòu)的損失。對(duì)于這里的欺騙手段�����,不能理解得過(guò)于寬泛���,必須是就“重要事項(xiàng)”的欺騙��,即限于可能嚴(yán)重影響金融機(jī)構(gòu)對(duì)借款人資信狀況����,特別是還款能力加以判斷的實(shí)質(zhì)性事項(xiàng)���。說(shuō)到底�,只有在行為人編造涉及抵押物價(jià)值�、資信證明等虛假材料�����,導(dǎo)致金融機(jī)構(gòu)高估其還款能力時(shí)����,才可以認(rèn)為行為人使用了“欺騙手段”����。的確,就所謂“重要事項(xiàng)”進(jìn)行欺騙�����,會(huì)影響金融機(jī)構(gòu)放貸時(shí)的自由決策��,如果金融機(jī)構(gòu)知曉相關(guān)真實(shí)情況�,就會(huì)基于風(fēng)險(xiǎn)控制等考慮而不予發(fā)放貸款,但這也僅僅是證立了“欺騙”與“發(fā)放貸款”間存在因果關(guān)系���,并不能證實(shí)后面的“重大損失”也是由欺騙導(dǎo)致���。過(guò)往的實(shí)務(wù)也往往忽視對(duì)“欺騙導(dǎo)致重大損失”的證明,實(shí)際上以“取得貸款”作為“因”替代了“欺騙”。在鋼濃公司����、武建鋼騙取貸款案中���,武漢市中級(jí)人民法院認(rèn)為�����,被告單位鋼濃公司及被告人武建鋼在申請(qǐng)貸款過(guò)程中���,提供虛假證明文件,夸大償付能力�,以欺騙手段取得光大銀行青山支行保理融資款2000萬(wàn)元,并導(dǎo)致1503.5萬(wàn)元不能歸還��,給銀行造成特別重大損失���,均已構(gòu)成騙取貸款罪�����。對(duì)于以欺騙手段取得融資款后是如何“并導(dǎo)致”1500余萬(wàn)元不能歸還的��,其間欠缺必要的證明����。不過(guò),恐怕不是審判機(jī)關(guān)不想去證明���,而是難以證明�����。于此��,可以參考臺(tái)灣地區(qū)刑法重利罪的規(guī)定���。該罪在構(gòu)成要件中之所以不要求“財(cái)產(chǎn)損失”要素,是因?yàn)橐_立“公平價(jià)格”的范圍極為困難����,可能牽涉到不同時(shí)點(diǎn)上的供給和需求關(guān)系、個(gè)人對(duì)于未來(lái)事件的評(píng)價(jià)標(biāo)準(zhǔn)�、資本生產(chǎn)力以及財(cái)貨的邊際效用等因素,在公平利率的確定上���,又與工資率�����、勞工數(shù)量����、現(xiàn)有可供支配雇傭工人的資金多寡、競(jìng)爭(zhēng)的人數(shù)�、因生產(chǎn)期延長(zhǎng)縮短所致的生產(chǎn)能力等級(jí)的改變等諸多因素有著密切的關(guān)聯(lián)�,在因果上欠缺透明性。以當(dāng)今的立法技術(shù)而言����,想要將這些因素充分考慮之后,再來(lái)確定實(shí)害的界限�,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(wù),因而只能采取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制裁結(jié)構(gòu)��。在騙取貸款罪中����,同樣存在因果關(guān)系難以認(rèn)定的問(wèn)題。通常認(rèn)為���,就“可能嚴(yán)重影響金融機(jī)構(gòu)對(duì)借款人資信狀況特別是還款能力判斷”的事項(xiàng)進(jìn)行欺騙���,取得貸款后發(fā)生不能還本付息的����,成立典型的騙取貸款罪�����。問(wèn)題是��,借款人的資信狀況是流變的����,借款時(shí)沒(méi)有欺騙且資信狀況良好不意味著能正常還本付息,借款時(shí)資信狀況較差且對(duì)此進(jìn)行欺騙也完全可能后來(lái)正常還本付息����,是否會(huì)造成金融機(jī)構(gòu)重大損失主要是由使用貸款的狀況決定,或者說(shuō)���,能否正常還本付息很多時(shí)候是一種“偶然”�����。既然如此��,如何能肯定欺騙行為與重大損失之間具有條件關(guān)系��?
就故意內(nèi)容來(lái)說(shuō)�,騙取貸款的行為人只是以“騙”取得貸款,并非以“騙”造成重大損失��。如果“重大損失”是典型的結(jié)果要素�,就需要行為人對(duì)重大損失具有故意,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(huì)造成金融機(jī)構(gòu)的重大損失(不能還本付息)�����,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(jié)果的發(fā)生��?����?墒?��,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不能還本付息,依然以欺騙手段向金融機(jī)構(gòu)申請(qǐng)貸款����,就已經(jīng)符合了貸款詐騙罪的主客觀要件����,而不能僅以騙取貸款罪論處���。
綜上�����,騙取貸款罪不是實(shí)害犯�,其中的“重大損失”只是作為客觀處罰條件的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��。
(二)“處罰條件”的立法論反思
刑法學(xué)上公認(rèn)�,結(jié)果犯的成立,以行為與結(jié)果之間具有因果關(guān)系為必要條件����。按照條件說(shuō),當(dāng)能確定沒(méi)有行為就沒(méi)有結(jié)果時(shí)���,就可以肯定二者之間具有因果關(guān)系�。這一要求是基于預(yù)防目的而來(lái)����。對(duì)一般人而言����,如果處罰一個(gè)對(duì)結(jié)果的發(fā)生毫無(wú)作用的行為��,根本不能達(dá)成預(yù)防目的���。當(dāng)然�����,因果關(guān)系的判斷必然受到人類認(rèn)知能力的限制�����,只能在人類能力的極限內(nèi)進(jìn)行判斷。無(wú)論如何���,結(jié)果作為決定客觀不法的因素���,其必要條件是因果關(guān)系。問(wèn)題是�,因果關(guān)系能否比條件說(shuō)有所緩和?既然立法者已經(jīng)在實(shí)證法上將某種結(jié)果作為客觀不法的必要條件�����,試圖緩和條件說(shuō)的所謂“風(fēng)險(xiǎn)提高理論”就不能被接受。結(jié)論是��,作為處罰條件的結(jié)果型情狀因不符合條件關(guān)系���,不是不法要素��,當(dāng)然無(wú)需為故意所及���。這種要素之所以出現(xiàn),是因?yàn)榱⒎ㄕ呦虢璐讼拗铺幜P范圍����,同時(shí)回避因果關(guān)聯(lián)和主觀罪過(guò)證明上的困難,形成了“抽象危險(xiǎn)行為+處罰條件”的構(gòu)造�。雖然已不是傳統(tǒng)結(jié)果犯而是抽象危險(xiǎn)犯,實(shí)證法卻仍保留了結(jié)果要素�,既像傳統(tǒng)結(jié)果犯,又像抽象危險(xiǎn)犯�,又像結(jié)果加重犯,使得適用復(fù)雜化�。
如所周知,對(duì)于客觀處罰條件的地位�����,存在激烈爭(zhēng)議。通過(guò)引入“需罰性”“不法→責(zé)任→處罰條件”的犯罪成立體系得到了有力提倡�����,即具備不法和責(zé)任只是說(shuō)明了“應(yīng)罰性”����, 在啟動(dòng)刑罰時(shí)還需考慮“需罰性”,客觀處罰條件只表示需罰性���。前者以評(píng)價(jià)因素為主�,后者著重預(yù)防目的�。問(wèn)題是:(1)犯罪行為的無(wú)價(jià)值評(píng)價(jià)和處罰的合目的性不可能分離,“應(yīng)罰性”與“需罰性”的對(duì)立�,會(huì)造成一種在絕對(duì)報(bào)應(yīng)刑論的基礎(chǔ)上“嫁接”完全異質(zhì)的預(yù)防刑論的印象。哪些因素屬于評(píng)價(jià)性的��,哪些因素屬于目的性的���,本就難以區(qū)分。根本原因是����,是否對(duì)行為作出負(fù)面評(píng)價(jià)�,如果不是從刑罰目的出發(fā)��,如何作出評(píng)價(jià)��?舉例來(lái)說(shuō)���,以“法益侵害”作為決定應(yīng)罰性的標(biāo)準(zhǔn)�,正是考慮到刑罰目的是預(yù)防新的法益侵害���,才有“需罰性”���,既然如此,應(yīng)罰性與需罰性就不可能區(qū)分����。即使為了理論分析方便區(qū)分二者,這二者也是同時(shí)在不法與責(zé)任�����、不法與責(zé)任之外的成立要件中都被一體考慮,而不是在不法與責(zé)任要件上只考慮應(yīng)罰性��,在不法與責(zé)任以外只考慮需罰性��。(2)“需罰性”會(huì)使得犯罪論體系內(nèi)部產(chǎn)生矛盾�����?�!靶枇P性”體現(xiàn)的是“值得處罰”這一整體特性�����,包含了不法與責(zé)任���,將其置入犯罪論體系��,就產(chǎn)生了用一個(gè)單一概念同時(shí)表示體系的“整體”與“部分”的理論矛盾�,陷入由“需罰性”為“需罰性”提供根據(jù)的循環(huán)論證�����。(3)“需罰性”概念不具有足以構(gòu)成犯罪論中獨(dú)立范疇的明確輪廓和具體內(nèi)容�����?���!爸档锰幜P”這一概念使得判斷對(duì)象必然是無(wú)所限定的,對(duì)于具有“分析性”的犯罪論體系而言�,賦予這種“綜合性判斷”以獨(dú)立評(píng)價(jià)階段的地位,顯然是不合適的����。綜上,作為抽象危險(xiǎn)犯處罰條件的結(jié)果型情狀����,難以在犯罪論體系內(nèi)實(shí)現(xiàn)邏輯自恰。
以結(jié)果發(fā)生為處罰前提����,事實(shí)上必然有限制處罰的效果,刑罰對(duì)國(guó)民基本權(quán)利可能的侵害范圍縮?���。坏鄬?duì)而言��,《刑法》容許國(guó)民基本權(quán)利受到某種危險(xiǎn)行為侵害的可能范圍則擴(kuò)大。以丟失槍支不報(bào)罪為例��,附加“造成嚴(yán)重后果”的處罰條件��,成罪范圍縮小��,被處以刑罰的范圍也縮?����?���;但相對(duì)來(lái)說(shuō),丟失槍支后不報(bào)告�,會(huì)使危險(xiǎn)進(jìn)一步增高,如果《刑法》要等到造成嚴(yán)重后果才介入�����,勢(shì)必難以周延保護(hù)公共安全��。因此�����,在決定是否附加處罰條件時(shí),必須考量相對(duì)利益的保護(hù)�����,而不能不附理由地為了限制而限制�。更何況���,限制處罰范圍的方式很多����,可以在主觀要件上限制�,也可以對(duì)行為樣態(tài)作限制,并不一定只能附加處罰條件�����。既然抽象危險(xiǎn)犯也是結(jié)果犯���,那就完全可以選取某種與行為至少具有條件關(guān)系的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 來(lái)作為判斷危險(xiǎn)的“中間項(xiàng)”���,同樣可以起到限制處罰的作用。即使無(wú)法找到合適的“中間項(xiàng)”���,也可以只表述行為����,通過(guò)解釋論把握作為結(jié)果的抽象危險(xiǎn)。
五����、作為實(shí)害犯“違法性補(bǔ)強(qiáng)”要素的結(jié)果型情狀
在本文看來(lái),侵害個(gè)人法益的犯罪類型���,概念上都是結(jié)果犯���。只不過(guò),在解釋論上既有犯罪行為與侵害結(jié)果分離的狹義結(jié)果犯�����,也有犯罪行為本身已經(jīng)隱含利益侵害結(jié)果實(shí)現(xiàn)的廣義結(jié)果犯���。就后者而言��,無(wú)需另行檢驗(yàn)侵害結(jié)果的實(shí)現(xiàn)���。如公然侮辱他人的行為��,就已經(jīng)隱含了毀損他人名譽(yù)的結(jié)果�。這種結(jié)果從經(jīng)驗(yàn)上可以觀察得知���,因而是一種“實(shí)害”�����,只是“無(wú)需檢驗(yàn)”罷了,是抽象危險(xiǎn)犯中“無(wú)法檢驗(yàn)”的所謂“實(shí)害”�。但是,因?yàn)槿狈ΚM義結(jié)果犯那樣直接的實(shí)害描述��,立法上可能需要利用結(jié)果型情狀要素進(jìn)行違法性補(bǔ)強(qiáng)����,以使其達(dá)到可罰程度。
一種情形是���,在刑法分則條文以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����、情節(jié)惡劣”作為成立犯罪的條件時(shí)����,司法實(shí)踐有時(shí)會(huì)將體現(xiàn)該罪法益外另一種法益對(duì)應(yīng)的結(jié)果或者明顯超出行為通常射程范圍的結(jié)果作為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�����、情節(jié)惡劣”的表現(xiàn)����。例如����,《刑法》第246條規(guī)定的侮辱、誹謗罪要求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����,《網(wǎng)絡(luò)誹謗解釋》第2條規(guī)定,“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�����、自殘��、自殺等嚴(yán)重后果的”��,屬于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的情形���。又如����,《刑法》第248條規(guī)定的虐待被監(jiān)管人罪也要求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,最高人民檢察院2006年發(fā)布的《關(guān)于瀆職侵權(quán)犯罪案件立案標(biāo)準(zhǔn)的規(guī)定》(以下簡(jiǎn)稱《瀆職罪立案標(biāo)準(zhǔn)》)將“虐待被監(jiān)管人�,情節(jié)嚴(yán)重,導(dǎo)致被監(jiān)管人自殺�、自殘?jiān)斐芍貍⑺劳?��,或者精神失常”作為立案?biāo)準(zhǔn)之一���。侮辱���、誹謗罪的法益是他人名譽(yù),造成被害人自殺等嚴(yán)重后果對(duì)應(yīng)的法益顯然不是名譽(yù)而是生命�����、健康法益����。虐待被監(jiān)管人罪的法益是人身自由�����,雖然可以延伸保護(hù)人的生命�����、健康�,但導(dǎo)致被害人自殺等后果顯然超出了虐待行為通常的射程范圍�。正因?yàn)槿绱耍谏鲜銮樾沃?���,司法解釋一方面將自殺、自殘等結(jié)果歸屬于行為人的行為���;另一方面又沒(méi)有讓行為人承擔(dān)故意殺人罪���、過(guò)失致人死亡罪等罪的刑事責(zé)任,明顯不同于通常的結(jié)果歸屬�。上述司法解釋使得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的立法中包括了結(jié)果型情狀要素。
另一種情形是�,刑法分則條文雖然沒(méi)有將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、情節(jié)惡劣”規(guī)定為犯罪的成立條件,但由于法條文字表述可能導(dǎo)致處罰范圍過(guò)于寬泛�,事實(shí)上需要情節(jié)嚴(yán)重、惡劣才能以犯罪論處時(shí)���,為了限制處罰范圍��,司法實(shí)踐也會(huì)采取前一種情形的做法����。例如���,刑法規(guī)定的刑訊逼供罪���、非法搜查罪、非法拘禁罪��、暴力取證罪����、報(bào)復(fù)陷害罪沒(méi)有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的要求��,但《瀆職罪立案標(biāo)準(zhǔn)》規(guī)定�����,“導(dǎo)致被害人自殺、自殘?jiān)斐芍貍?��、死亡���,或者精神失常的”,均?gòu)成相應(yīng)的犯罪�,成為成立犯罪的一種情形?���!稙^職罪立案標(biāo)準(zhǔn)》將體現(xiàn)某罪法益外另一種法益對(duì)應(yīng)的結(jié)果或者明顯超出行為通常射程范圍的結(jié)果作為犯罪成立標(biāo)準(zhǔn),使得結(jié)果型情狀要素實(shí)質(zhì)上成為犯罪成立條件�����。
有學(xué)者認(rèn)為���,在前一種情形中����,“情節(jié)”并無(wú)限定�,只要是表明行為不法的情節(jié)即可,自殺等結(jié)果雖然不能進(jìn)行通常的結(jié)果歸屬,但畢竟是構(gòu)成要件行為所引起���,可以認(rèn)為增加了不法程度�;但在后一種情形中���,引起自殺等只是單純的客觀處罰條件���。在本文看來(lái),刑法分則條文是否規(guī)定了“情節(jié)嚴(yán)重”“情節(jié)惡劣”并非重點(diǎn)����,不能因是否有這種規(guī)定而使結(jié)果型情狀存在不法要素與處罰條件之別。關(guān)鍵在于�����,在兩種情形中��,結(jié)果型情狀都是由構(gòu)成要件行為引起�����,仍在“行為不法”的射程范圍內(nèi)�,因而是對(duì)違法性進(jìn)行“補(bǔ)強(qiáng)”的要素??陀^處罰條件不可能與構(gòu)成要件行為存在條件關(guān)系,不具備不法要素的資格����,不存在結(jié)果歸屬的問(wèn)題。
可以肯定�����,上述犯罪并不是以“情狀”為結(jié)果的實(shí)害犯�。侮辱、誹謗行為一般會(huì)造成被害人名譽(yù)的貶損��,但這種實(shí)害無(wú)法具體判斷����,所以理論上一般認(rèn)為其是抽象的危險(xiǎn)犯。也有學(xué)者認(rèn)為�����,抽象危險(xiǎn)犯還包括刑法擬制的實(shí)害����,侮辱����、誹謗罪可以認(rèn)為是擬制的實(shí)害犯�。不難發(fā)現(xiàn),上述兩種情形涉及的都是侵犯自由�、名譽(yù)、民主權(quán)利的犯罪���,只要完成構(gòu)成要件行為��,難以想象對(duì)于被害人沒(méi)有產(chǎn)生相應(yīng)法益的實(shí)害����。既然行為本身在經(jīng)驗(yàn)上幾近絕對(duì)代表著法益侵害結(jié)果的存在�����,就不值得再動(dòng)用司法資源對(duì)于實(shí)害的存在作原則性的審查��。據(jù)此����,這些犯罪都是實(shí)害犯。從構(gòu)造上講���,“行為”表述涵攝了“行為造成權(quán)利損害的實(shí)害”�,其后的“結(jié)果型情狀”是對(duì)前面實(shí)害犯違法性的補(bǔ)強(qiáng)�,不會(huì)改變實(shí)害犯的本質(zhì);結(jié)果型情狀適用緩和的結(jié)果歸屬�,主觀明知與希望或者放任的結(jié)果是前面“行為造成的實(shí)害”,對(duì)后面的結(jié)果型情狀只要具有認(rèn)識(shí)即可�����。
結(jié)語(yǔ)
《刑法》的功能在于保護(hù)法益����,但法益是一個(gè)抽象、觀念性的關(guān)系概念���,因此����,一個(gè)具備刑事不法的法益侵害有必要通過(guò)結(jié)果要素予以表達(dá)��,從而使抽象����、觀念性的法益能在人類既有的認(rèn)知基礎(chǔ)上連接至經(jīng)驗(yàn)性的侵害狀態(tài)�����。換言之�,行為的刑事不法系由一個(gè)具體可感知的損害結(jié)果回溯地確認(rèn)���。隨著社會(huì)結(jié)構(gòu)的變遷���,特別是工業(yè)化、資訊化及科技化的發(fā)展���,社會(huì)系統(tǒng)的運(yùn)作更趨復(fù)雜��,社會(huì)活動(dòng)可能招致更多潛在的侵害風(fēng)險(xiǎn)��。為了讓法益保護(hù)更為周全且更具效率��,立法者廣泛采用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模式�����,積極介入個(gè)人自由領(lǐng)域�����,甚至是滿足純粹的行為控制需求����。即便如此�,抽象危險(xiǎn)犯的立法設(shè)計(jì)與解釋,仍然必須遵循“行為引起結(jié)果”的原則��。鑒于抽象危險(xiǎn)犯結(jié)果的危險(xiǎn)狀態(tài)難以具象化表達(dá)�,只能借由某種“中間項(xiàng)”要素間接證明,“結(jié)果型情狀要素”就起到了這一溝通作用�����。在超個(gè)人法益犯罪中�,需要審慎甄別直接表述結(jié)果本身的結(jié)果要素與間接證明結(jié)果的“結(jié)果型情狀要素”。當(dāng)某種“結(jié)果型”要素與行為具有事實(shí)因果關(guān)聯(lián)但不符合通常的歸屬要求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就是判斷抽象危險(xiǎn)的“中間項(xiàng)”����;如果某種“結(jié)果型”要素與行為間連事實(shí)因果關(guān)聯(lián)都不能肯定,那就只是作為限制抽象危險(xiǎn)犯處罰范圍的條件�。但以結(jié)果型情狀作為單純處罰條件����,面臨犯罪論體系上的矛盾����,在立法上要謹(jǐn)慎使用。此外�����,在部分侵犯?jìng)€(gè)人權(quán)利的實(shí)害犯中��,結(jié)果型情狀能發(fā)揮對(duì)既有實(shí)害結(jié)果的“違法性補(bǔ)強(qiáng)”作用�����。
因篇幅限制��,已省略注釋及參考文獻(xiàn)�����。原文詳見(jiàn)《河北法學(xué)》2024年第3期���。
